不久前,人类学家项飙的新书《你好,陌生人》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是一系列发生于2023年的对谈的集结——当时正处于疫情尾声,项飙与画家刘小东、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等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艺术家对于“社会陌生化”展开的一系列对谈。
距离那场对话的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陌生化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升级”了。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AI的普及,让人们的情感依赖出现了新的转向;而线下的真实关系则变得更脆弱、疏远。
7月初,我们跟项飙老师围绕着AI、年轻人与陌生化进行了一场对话。这不是一次对新书的补充说明,而是对当下社会状态的再观察。
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全面迎接AI社会。但在那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先学着辨认一个人身上的“活人味”。因为只有在那里,真实的社会才能开始,人与人的信任才可能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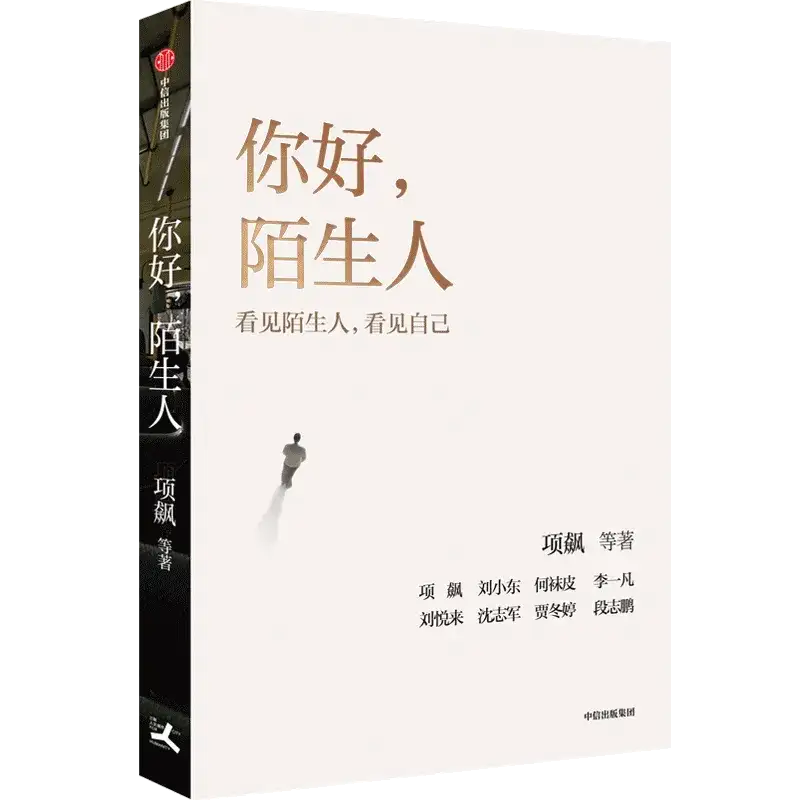
《你好,陌生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是人类学家项飙领衔的一部剖析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作品。
以下为后浪研究所(简称后浪)与项飙的对话:
后浪:之前大家还在谈论附近的消失,很多人会忽略身边的人,到网络上去跟更远的人交流。而现在我们发现,很多人可能都放弃跟人交流了,他更愿意去跟AI或智能体聊天,而且会对AI产生情感依赖,国外甚至有一些极端案例是人跟AI的虚拟影像结婚,真实的人际交往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只跟AI说话”的趋势,您会担心吗?
项飙:我对这个趋势是担心的。但是我们要看到,AI给人带来的焦虑不是AI本身,这个要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理解。一方面,AI出现的时刻,正好是经济下行、人们生存压力加大、悲观迷茫情绪蔓延的时候,AI的出现带来了巨大的兴奋、新鲜感,大佬们、资本、政府都在非常热情地宣扬,好像AI会有神奇的力量,带我们走出低谷,带来一个全新的未来。但另外一方面,对于年轻人个人来讲,AI又是让他们恐惧的,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取代他的工作、情绪,甚至控制他生活的这么一个技术。
这样的个体的感觉和亢奋的总体叙述放到一块,就会有一种好像我是历史潮流里面的一个陌生人的感觉。觉得我不了解历史潮流,历史潮流也不会关爱我,我也许会成为被历史潮流淘汰的一个对象。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陌生化可能变得更加的深入,更加广泛。对AI产生情感依赖,其实也是这个陌生化趋势的反映。
后浪:那这种趋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项飙:把AI作为一个情绪的诉说对象寻找温暖,不仅是附近的消失,而且是一定意义上人的消失。
AI为什么那么吸引人?AI的恋人为什么是完美恋人?因为它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设计的。不管AI如何塑造成非常丝滑地跟你对话的这种方式,它不可能给你带来独特的基于生命经验的视角,因为它没有一个独立的生命经验,不可能调用它的具体经验对问题进行分析,它只能对你的情绪进行迎合。所以它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交流,不过是一个比较高阶的回音壁,或者你的影子。现在AI把“顾影自怜”四个字彻底地实现。
当你对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世界本身就显得很模糊和可怕。你在工作生活中,别人不可能是你的影子,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觉得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好像角斗场一样,而不是觉得大家跟我不一样好有趣,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看不到人了。
后浪:这听上去很悲观。
项飙:但这里又是有希望的。他如果是完全顾影自怜的话,为什么还要用AI去塑造一个影子?说明他还是要对话,希望听到回应。
这揭示出人的一个基本本性,就是对自我的认知是一定要通过一个他者的存在,否则也没有必要找个AI说话。现在的危险是,渴望被误导成了跟影子对话。青年朋友们可以去想,这个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生命的声音,为什么对你重要?
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也许能够帮助大家走出一步,去找真正的别人,也许真正的别人给你的反馈会更强有力,也许让你有的时候会噎住一下,让你惊讶,让你不爽,但他会真正调动你跟别人的连接性,调动你的反思。
后浪:但首先要长出这个意识才行,才能把自己拉出来。
项飙:是的。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思路,不是说怎么远离AI,而培养出另外一种有力量的交往方式,让你觉得它比AI更吸引人。为什么要重建附近,或者对具体的陌生人进行想象(我们做“你好,陌生人”项目之前的一个想法是动员大家对自己身边经常看见的陌生人进行书写,猜这个人是什么情况,他心里最大的焦虑是什么?他期望什么?家庭可能是怎么样的等等),就是这个意思。通过这样一种干预和行动,大家觉得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去想象生活,跟人互动,去抒发自己心里各种各样的感受,你就不会那么依赖AI。
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和东亚社会AI势头特别强烈?原因不是AI技术本身,而是生活本来已经变得非常稀薄,大家没有太多的能力或精力去跟自己的周边和陌生人进行互动,他本来就有这种孤独和恐惧在那里,然后AI一来好像给他解决了很多问题。他就觉得跟AI好像更契合,所以他不仅是顾影自怜,他还一见如故了。
在AI来之前,我们整个的教育和工作系统的行政化,变得越来越形式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AI化了。我们不是去寻找那些跳跃性的思维、横向思维,也不靠和具体个人的互动来满足情绪的需要,我们越来越多依靠符号、象征,抽象的规则来演绎和反思。所以我们现在的困境也不能够一股脑的都赖在AI上面。比方说自我封闭和社恐,这在原来的网络时代已经存在了,只不过AI把它更强化了。既然问题的根本不是AI,那它的出路也不是要不要AI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在AI之余是不是还有生活的问题。

人类与AI聊天,电影《梦境》剧照
后浪:这让我想到三年前,我们写过的一篇关于“女性夸夸会”的报道(《北京女子夸夸会:被漂亮女孩连夸2小时,我上头了》)。在北京的一家小店里,每周会有一个晚上举办一场全部为女性参加的“夸夸会”,进去后大家会互相夸赞,比如夸你五官立体、口红好看或者很有品味等,然后讲述各自的故事。也算是一种新型的社交,而且类似主动创造的社交活动其实蛮多的,大家也会积极主动地去参与,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在社交上用力过猛。但最后能进入并维持更深层次关系的貌似很少。
项飙:我很好奇,我要去那些夸夸会,别人会怎么样夸我。(笑)
大家愿意做这样的努力是很可贵的,还是希望见到人。我没有参与过,也许会变成了某种幽默喜剧大会,大家可能夸得很有创造性,对是不是真夸也不太在意,都哈哈大笑。人和人走到一起,不管他的场景或者原来的目的是多么奇怪,只要你不去刻意的表演或者有目的的欺骗,一般都会有一些有趣的互动出现。
像夸夸会听起来也可能会增强人的陌生感。大家带着这种目的来,然后一个劲一股脑的要夸对方,被夸了之后你又觉得有义务夸回去。这样不仅不能进一步了解彼此,而是说你通过怎样的行为去维持距离不变。夸夸会要把关系维持在词语的互夸上。在夸夸会上你可能不会说,我上午化妆化了三个小时,烦死;或者这衣服其实穿着一点都不舒服,被骗了。如果讲这个话,对方会觉得很可爱,你如果不讲,其实你穿着衣服很不舒服地坐在那里,就意味着你要不断的动员自己的心力,去保持住这个状态。你要对自我进行监控,对别人进行监控,给别人压力,让他们监控自己,维持关系不变。陌生化就是刻意维持陌生关系,生怕变熟悉,因为变熟悉不知道怎么样处理。
像夸夸会,都可以是实验,哪天我就化妆得特别丑,看一下大家怎么夸,这里就需要一种创造性和一点点勇气,我抛出这份刺激,看别人怎么样回应,然后互相打开。而不是去印证自己的美丽和能够夸美的能力,那是一个陌生化的持续。
后浪:但现在大家都很怕暴露自己的缺陷,前阵子许知远老师也在一次活动上提到,说现在大家都很怕出现纰漏,发个朋友圈要反复地P图,修改文案。似乎大家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完美。但另一方面,像您刚才说的,化了三小时的妆很烦,这种打破一些关系边界的坦诚,或者瑕疵的暴露,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爱和喜欢,因为有“活人味儿”。“活人味儿”这个感受实际上是非常受人追捧的,那您觉得这两种现象之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项飙:这里的底层逻辑有两层。一层是本真性,你看见别人这么完美,就有压力;把自己搞得完美,但知道这个不是真的,看到别人也知道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就变得比较虚幻,不知道世界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是让人感到很无力的。
大家喜欢说真话,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的本性,而是你说真话以后会越说越多,越说越细,越说越深,越说越有味道。这是把不同的经验给调动起来,从一个侧面走到另一个侧面,你就感到自己很丰富,是一个自我培育、自我壮大的过程。
说假话是你逼着自己为一个说法服务,一会儿就耗空了,你的经验不能够支持这些话,你觉得自己是被否定的对象,我不完美。本真性才有持续性。
第二个是互动性的需求,这和对本真性需求是直接相关的。有活人味之后,你就自然地觉得这人可交可说,你的一点瑕疵激发了我更多的东西,交流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和有趣。如果一切完美,那就不是交流,是你呈递一个文本,我再给你呈递一个文本,如此而已。
为什么要大家用“活人味儿”这个词,它显然是跟AI这样一个完美的非活人(相对的)。AI现在主要还是大语言模型,把世界上存在过的语言尽量都搜集起来,哪一种表达出现的最多,它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模型,你看起来当然很顺眼,因为你本来看它就看得多。以什么标准我们把一个形式叫完美?无非就是它最符合多数人的最没有反思性的习惯。它就是冲着所谓大众形成的完美观来的。但它不呈现个性。
“活人味儿”是个重要的意识,我觉得应该去提倡的。

摄/何勇
后浪:“活人味儿”在某些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松弛?您觉得松弛与紧张这两种状态在当下的集体呈现,跟AI有怎样的关系?
项飙:AI可能是很容易让人紧张的。我自己没有用过AI,我这个是想象,可能说的不对,比方说我要写文章,它生成的文本让你觉得很难去超越,框架完美清晰,语言表达顺溜……你能看出来这话不像人说的,但是它好像又很强大,让你说不出比它更好的东西,有种很憋气的感觉,这就让你很紧张。
人紧张就是他不能够跟自己比较和平地处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不太对,要额外地咬咬牙把自己修正一下。你好像是跟AI比赛,觉得AI是提醒自己的不足,不知道怎么能够比AI写得更好,这样对自己的价值和原有的特色,自己的生命经验都产生一种怀疑,你就会紧张。
但作为一个思考者,我要做的不是完美而是特性,所以我一定要很松弛的,要注意到自己的特色在哪里,我讲出的东西肯定不如AI完美,但我有一个特色的东西是AI捕捉不到的,因为这个特色在既定的话语里还不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松弛就意味着自信,你能不能够松弛或者自信到这个程度,把特色表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们今后的评价体系,独特的角度、你个人的角度是怎么样从经验里来的,就会变得比较重要。
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写文章不太注意这些。比如学校里的作文,大学里的调查报告,公司里面的这种报告都是没有活人味儿的,我刚才就说不是因为AI来才没有活人味儿,是AI到来之前就各种八股,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一个AI的工具。现在又到了一个节点,就必须把活人味讲得更加彻底,要更有意识地去培养这个东西。
但怎么样去转变,因为它涉及到评价体系,老师改作文的时候怎么改,公司里什么样的报告领导看了觉得好,这需要一步一步去通达。
后浪:另外,在我们的观察中,发现有越来越多病症都出现了年轻化趋势,比如卵巢早衰、癌症、糖前期等等,甚至性欲的降低,这都成了我们报道的一个“赛道”。我们最新关注到的是慢性疲劳综合症,所表现出的症状跟前一阵网络上流行的“低能量人群”很像,常感到疲惫、睡眠紊乱、出现“脑雾”等。这种普遍性的低能量,让人感觉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生命力是很稀薄的,您觉得他们是真的没劲,还是不想有劲了?
项飙:我以前谈到过生命力,大家说身体上感到疲劳无助,不能睡眠等等。他即使身体上没有明显的症状,主观上也觉得打不起精神,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总是采取一种怀疑或者戒备的心态,老是怕出问题,这本来就是一种生命力的下降,他不敢试错。在这样一个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人是很容易孤独的,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亲密联系,这会让你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心理疾病不断上升。
这是我的一个假设:也许AI之下我们会出现一种漫长的赖活着的状态。一方面AI在医疗领域应用很多,它可能会在制药、诊断上面越来越精细,越来越高效,它不断给你非常精确的诊断,把你救过来,不让你死掉。另一方面AI可以让你生各种各样的病,你活着是没有劲,没有精神的,疲劳的。所以长期“赖活”着可能是AI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

图源unsplash
后浪:长期赖活着,这听着很难受。
项飙:我觉得很可能会是这样,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跨入这个情况了,怎么样把它转化为一种更加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后浪:如果说有些人已经意识到需要长期就这么赖活着了,他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比如躺平,躺平之后心态放松了,可能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项飙:对,大家是做了很多尝试了,哪怕很小的火苗,这种实验都是值得去鼓励的。
但问题是,躺平是消极的,躺平本身不太能给人的生命提供能量,因为你必须有生命力,要让自己兴奋,让自己的个性凸显出来。
如果只是躺平,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或者完全没有计划去哪里,过一是一天,其实是很消耗的,在很多情况下,它比你工作忙的时候可能更消耗。你的存在是需要有方向感的,要有一种我在往前走,在不断强化自己,不断学到新的东西得感觉。这种感觉如果没有,我觉得躺平也不能够持续。
后浪:因为有时候躺平在某种意义上,会让人觉得是心理上的一种放松,可能我没那么焦虑了。
项飙:放松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你跑完步之后坐下来歇一会儿,放松。另一种更重要的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放松,就意味着某种自信,我跟我自己的关系非常融洽,我让自己的情绪,包括有时候非常紧张、非常愤怒,能自由地表达出来,那是真正的放松,那种松弛给你力量。
后浪:我们还观察到,除了这种“赖活着”的低能量感,还有一种与之相对的非常极端的情绪状态,就是“发疯”。尤其是在一些等级关系中,比如职场上下级,或者是原生家庭中孩子与父母之间等等,偏弱小那一方会在某种场景下靠“发疯”夺回自己的掌控权。举个例子,父母在青春期的孩子卧室偷偷装监控,孩子发现后没作声,也偷偷在父母房间装了一个,之后把父母同房的视频直接发到了家族群里。您如何理解类似的这些行为?
项飙:这很有意思,发疯好像是人性爆发了。你刚才概括得很好,他不简单说是抵制,说你不应该给我装监控,你要认识到你的错误,你要道歉……他不管这个。他是以剧烈的方式,让你这次行为不能成功,而且下次不敢对我怎么样。所以这个概括是很有意思的,夺回自己的掌控权,或者说重新划清一个边界,并不是一个权利法理上的论证,而是让这个后果变得你无法承担。
但是发疯会不会成为一个对社会结构规则有改变的(力量)?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它发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比方你举的例子里面,可能他的家庭关系或者公司内部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双方都会处于一个长期紧张的状态,双方都会有很多阴影的。
这跟AI也有一点关系,如果我们的社会规范越来越AI化,会让人变得无法辩驳,当人觉得自己的个性独特性没法得到阐释的话,他只能用发疯的方式来表达。
各种的KPI,各种时间的计算,就是让你觉得没有人可以商量。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好像不那么等级化了,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站在那里对你指手画脚,但你要面对一个很抽象的AI,其实会更让人发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以人的方式表达。这就回到《你好,陌生人》里讲到的两种公共性——一种公共性是靠无数的横向关系,你和我的关系,他和我的关系,这样具体的人具体的行动叠加出来的公共性。另一种公共性就是平台一样的公共性,AI就是它给你造出一个很大的公共性,但你和我是没有实质关系的。
在这样的平台式的公共性面前我们都是裸露的。它能够看穿我们,你和我是看不明白的,也没办法交流的,大家的眼睛都是对着那个第三方平台,这种新的公共性下面,发疯就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人和人之间进行交流、反思、协商的一个基础。

2023年项飙在温州做调查 摄/何勇
后浪:感觉现在没有什么中间态,要不然就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特包子,一味退缩妥协,直到最后不能再退了,发疯。
项飙: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怎么样发展出中间的技巧,能够以更加说理或者协商的方式确立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边界,这是需要思考的,也是在我们教育过程当中是非常缺乏的。
我们想象当中的社会好像就是一个整体,一套规则,像一个铁桶,要么你就是退,要么你就是疯,他看不到里面还有很多具体的关系和可以协商的空间的。但这个是需要技巧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重建附近,大家要学会理解社会和生活是怎么样具体构成的。
后浪:您也提到了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去需要学习的,包括所谓的中间态,你要跟别人去协商去沟通,去改变跟周围人的相处模式,我们应该从哪一步先开始?
项飙:现在是有这样的苗头,很多学生会去参与社区工作,哪怕在校园里观察食堂系统是怎么回事、环卫系统是怎么回事,他们劳动关系是怎么处理的等等,这里可以有很多很深的学问,任何人了解这些之后,就会对人性的丰富性有更好的掌握。如果你不理解人性的丰富性,你很难建立对人性的信任。
中学比较难,管得很死,我觉得家长应该有意识地向学生展示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带着他去旅游住四五星级酒店,以那种方式显示自己对孩子的爱,你多讲讲自己真实的成长过程。
人性的美好往往是在不经意当中呈现出来,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一层,多注意自己和被人在不经意当中流露出来的善良、智慧和力量,你会更自信,也对社会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
文章来自于微信公众号“36氪”。
【开源免费】Browser-use 是一个用户AI代理直接可以控制浏览器的工具。它能够让AI 自动执行浏览器中的各种任务,如比较价格、添加购物车、回复各种社交媒体等。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browser-use/browser-use
【开源免费】AutoGPT是一个允许用户创建和运行智能体的(AI Agents)项目。用户创建的智能体能够自动执行各种任务,从而让AI有步骤的去解决实际问题。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Significant-Gravitas/AutoGPT
【开源免费】MetaGPT是一个“软件开发公司”的智能体项目,只需要输入一句话的老板需求,MetaGPT即可输出用户故事 / 竞品分析 / 需求 / 数据结构 / APIs / 文件等软件开发的相关内容。MetaGPT内置了各种AI角色,包括产品经理 / 架构师 / 项目经理 / 工程师,MetaGPT提供了一个精心调配的软件公司研发全过程的SOP。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geekan/MetaGPT/blob/main/docs/README_CN.md